细细算起来,她离开这个家,已经快到二十年了。当时她离家的时候,那和他生的孩子才五六岁。
实际她原来那男人并不错。那男人,原来读书是很好的,因为家庭实在太穷,所以一心想跳龙门。后因偶尔中考失利,大病一场之后没奈何回来跟人家学了一门木匠手艺。整日里也不多说话,径自早出晚归。记得当时在村人眼里,那是一个很把苦的男人。
她是他花钱从外地买来的。没法子,当年他家和全国人民一样,兄弟姐妹多,家里更穷,说“上无片瓦,下无立椎之地”毫不为过。总不能看着家里儿子打光棍,老实巴交的父母找亲访友托人从外地勾连上一女子来。那云南女人来时,是连云港一骑摩托车的送过来的。钱付给那中间的人贩子后,那送货的车手好像临走时还敲了八百多元现金,说是“没功劳有苦劳”。笔者到现在都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那女人可能原本就“来者不善”,这之前“中转”了多少家,没人知道。乡下人虽说纯朴第一,但久被外人欺骗,也自然“久病成医”。自打这女人来后的当晚,村人散去后各自回家,中间瞎想的人多了去了。其中有头上梳油滴滴的有点嫉妒心的婆娘就开始在自家男人床头开始嚼舌头根了:
“不知是三货还是四货,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杨柳,长挑身材,瓜子脸儿,浑身白肌芽芽、细皮嫩肉的,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说话娇滴滴能把男人心勾出来膛来,再看那眉梢带着一股媚劲,哪像一个种地人家出来的?会不会跑呢?防着点!”
不过那女人过门后,肚皮也争气,第一胎就生了一个小子。家境确实继续贫困,只是那男人更能苦(钱)了,早上天没亮出去,晚上天黑漆漆回家。那女人天天在家带孩子,晚上忙碌一天的男人回家,急赶紧替他脱衣解带,伺候茶汤脚水,百般殷勤扶侍。到夜里枕席送欢,无所不至。这日子虽粗茶淡饭,一家子倒也平安无事。
随着孩子过了三朝八月会爬会走,那女人心就如猫抓一般,就想出去转转。守家的老人也没在意,想想儿媳已来到这个家门几年了,还生了一个男娃,不会再有走的心思吧?也就没有多想。
男人也看出自家女人闲得慌,就说那你有空就到街上转转。当地有两个集,一个在镇上,逢双成集;一个是下面自然久久形成的集市,落单有人。离家都不远,也就三四里路程。那女人找自家男人要了小伙钱,然后把家里那破自行车拾掇拾掇,没事农闲时就带那孩子,一会赶“小张集”,一会赶“王兴街”,偶尔秤一斤豆腐回家,也或割半斤猪肉两根油条,一家子也欢欢喜喜的。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因这妇人逢集上街,竟真应了那偈语:“春心一动如丝乱,任锁牢笼总是虚!”
书接上回。话说那“小张集”街北首桥头,有一修自行车的年轻后生,生母早逝,父子俩孤鳏未娶、相依为命。那孩子也是一把修车的好手艺,街头站得久了,嘴甜的很,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见人三分笑,待客自来亲。这孩子的外婆家和本文所说妇人所嫁婆家,均系一条庄上人氏,原本就认识那妇人。那妇人天天上街勤了,总有那破自行车不是车圈就是大皮内胎坏了的时节,就把那破车推到那孩子修车摊上修理。那孩子修车确实公道,收费不高,遇到自行车小毛病,扳子、钳子搞来搞去分文不取,那妇人更是娇滴滴感谢不尽。一来二去,那妇人和那孩子就熟了,闲聊中那妇人就知道那孩子的底细。
那俩人起初或都“郎无情、妾无意”,但那孩子年近二十六七,人原本也长得走得出去,只因为家贫父鳏,天天正愁没哪家姑娘正眼相看,哪架得住那丰姿嫩色的妇人天天来来回回从摊前走过有事没事打招呼?“要把她勾到!”这熊孩子心里开始发狠了。
这做男人的只要心里一活,那八百八十九个汗毛孔都来点子。原来搞修理的天天风吹日晒,满身脏污、邋里邋遢,渐渐的那孩子因为有想法在心,所以每天出门前拾掇得整齐。再遇到那妇人来修车,不论大小毛病直接一文不收,没事还聊些激情言语来拨那妇人春心。再说因久不收钱,那妇人面上也过意不去,就会从街上买些桃儿果儿递过来,把那熊孩子搞得神魂颠倒,心猿意马,七颠八倒,酥成一块,半夜三更趟在床上都臆想一番。
想那妇人原或就是风月场中过来人,什么男女之事没见过?思及自己“青春未及三十岁,欲火难禁一丈高”,再看那修车摊的孩子对自己有意生情,想想自己也才二十才出头,自家那男人,天天如木雕泥塑一般,又黑又廋,没日没夜只顾苦钱,隔三差五自己登鼻子上脸要个“房事”也如应景一般,哪有半丝情趣?难道自己这一朵鲜花一辈子就着落在这五寸丁、谷树皮上?
如今被这熊孩子一撩拔,这妇人心里立即活跃起来,径不顾自己上有夫、下有小,使尽手段,奉承其趣,颤声柔气,只摆弄得那熊孩子天天魂不附体,哪还有心思天天修车苦钱?
每日里,只见那熊孩子眼直勾勾总瞄着那妇人来赶集的路。唉!
这正是:“落花着意随流水,流水生情恋落花”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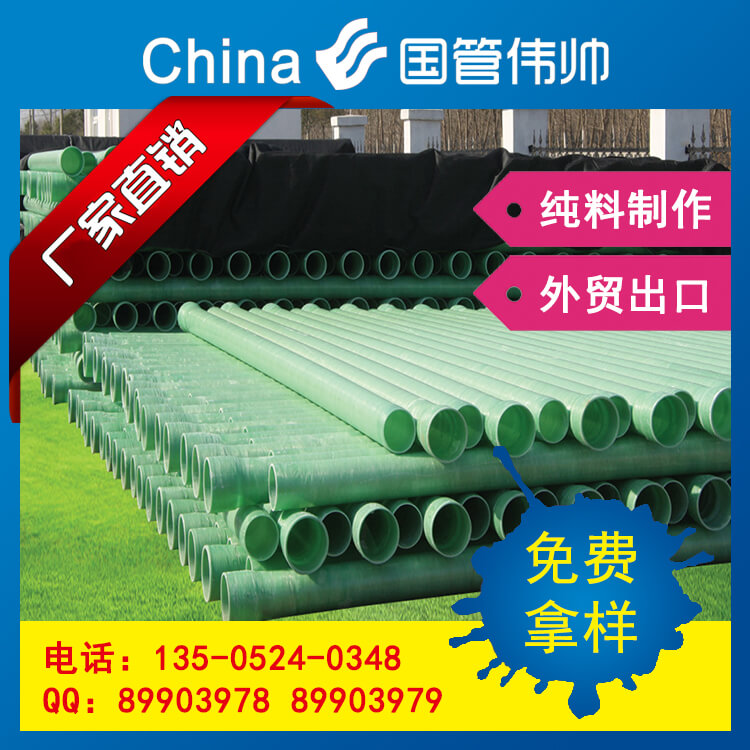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