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四点多,打一死党同学电话,意思是让他到我家拿他要的物件,可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晚上我带孩子去浴室洗澡时,他电话回拔到我手机上,问我“打他电话有何指示?”
“想你了,想请你到我家喝两杯酒”我嬉皮笑脸说。
我和他一样不擅喝酒也不喜喝酒,那东西一个是现在是“严打”,另外真的是伤肝害肺的没意思。我主要是想邀他到家坐坐聊聊的意思。他在电话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和我说:“哥啊,我哪如你舒服啊?我还在外做事呢,赵本山不差钱,我差钱!”
我知道年关要到了,各家都要拾掇拾掇家里的坛坛罐罐,室里室外也要打扫打扫,清洗油烟机的生意多起来了,所以他现在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他是我同学,一起从学校出来,凭着农村老百姓血脉里流淌的天生勤劳和不懈努力,经历阴错阳差,选择了适合各自生存的道路。他夫妻俩人有正在上高中和初中的两个孩子,一边维修家用电器,一边附带安装空调、拆洗油烟机的业务,他负责用摩托车帮客户拆装油烟机,他老婆则在家用一只大的塑料桶,把他和客户谈好价格带回来布满油渍的油烟机拆散后的骨架放在清洗液里擦洗干净,然后用电热吹风烘干,最后再认真组装好,让他再送还给客户家并再重新装上。
我这个同学不像我总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他特别开朗,豁达,嘴甜,说话像机关枪,在认识不认识的人面前啪啪的响。在出校门后,修了一阵家用电器,没饿昏也没涨死,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几年后,他跑到南京为人家送煤气瓶楼下楼上的又苦了几年,后来年龄大了又回到这个城市,重操旧业,可偏偏命有偏颇。有一次,因为好心好意用摩托车带一邻居出去,在路上那个邻居坐在车后面凭白的跌落下来,他来来回回跑医院服伺人家,最终赔了人家四五万人民币。
他那夫人性情和她男人恰恰相反,更不是那种“有钱的愿化作比翼鸟,无钱的恨不得就要插翅飞去”的女人,她天天心平气和,少语、寡言,不论自家男人在外如何的奔波劳碌,即使每天或不一定交回一点点为数不多的劳酬,她也从不抱怨,从不唠叨,更从没见过她恶语相向。
我没事时会从他店铺门前路过,一般不停车透过车窗玻璃,多看见他那一直笑容满面的夫人站在塑料桶前在认真擦试着油烟机,有时偶尔晚上到他店铺去玩,里里外外全是零零散散的电器,拆散架的油烟机,脚也插不进去。只见他夫人戴着长长薄薄的橡胶护袖在里里外外的忙着拆洗,我开始还会说:“你们清洗(油烟机)生意这么好,为何就不能多请一个人帮你们做?”。
他夫妻俩会异口同声的回说:“现在工资这么高,哪容易找到合宜的人啊?哪个又愿意沾这脏兮兮的东西?”我想也是,渐渐的就不开口提这个话题了。
他们俩口子对外人特和睦,他们店铺所在的前进街是这个小城市里多少年前就有名的老街,不讲理的,地头混角的,骄横跋扈的人不少,可多少年了,真就没听说他们俩口子和哪位吵过架、红过脸。
也许见过的世面多了,背后两个人在聊天时,也会撅天骂娘、针砭时弊,可生活中遇到不讲理的或“纵三纵四”的,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是他们俩口子一惯的行事原则。
一般情况下,男人晚上回家迟了,累了,他老婆早已做好香甜可口的饭菜,等他回来。他从不抽烟,也不喝酒,他们那俩个宝贝女儿也特别懂事,一点也不要她们爸妈操心烦神,一放学各自做自己的作业。
而作为父亲,他也有自知之明,以他两个女儿现在所学的东西早超过他,根本谈不上再辅导孩子学习的事,当然,更谈不上摆什么为父的架子,呵呵。
有的时候晚上需要接孩子回家时,他会一个人跑到十公里外的学校门外痴候着孩子放学,如不需接送孩子一般情况下,他会去马路边和邻居吆三喝四的下几盘象棋,不到九点就回去把车推到屋内,把店铺外的东西拾掇到里面,关门,熄灯,休息。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写漏了。我那同学和天下大多数男人一样,有点“惧内”。当然,这个“惧内”两个字,有多少种形式和解释,其中基于尊重和希望家庭和睦才“惧内”的原因占多数。记得他有一次,八点不到,和我一起在另一个死党家吃饭正潇洒着,不知哪一个开口提到家庭“领导”的问题,他还在胡吹乱侃说:“他家里人全听他的。出外玩,不要请示汇报的。”没曾想他话音还没落,挂在他裤腰带上的手机不迟不早的突然响了,他急急扔下筷子,抠出电话,一看是他老婆的。他老婆应当是知道和我在一起的,可能也只是提醒他少喝酒的意思。没曾想他接到电话竟和一般男人一样立时脸变色了,用手挡着话筒,作鬼鬼祟祟状,战战兢兢样,灭寂小声对电话另一端悄悄说:“一会儿就回去,还有十分钟!”
众人前仰后合,哄堂大笑!
此故事,后一直作为我和他几个死党在一起时的谈资,没事就拿出来,抖弄几句,呵呵,也是极开心!
说实在的,和他接触几十年了,我知道,他们的理想极平实,“顾好这个家,供两个听话的孩子上学,平平安安的好好再苦(挣钱)几年,多积赚点钱,在好的小区再买一套商品房,然后,再准备一点钱,好养老!”。
“靠别人,全是假的”这是他们一直挂在嘴边的话。
他们的店在前进街南端,面向西,离南边东西走向的淮涟路也就一百米的距离吧。
瞧,多好的一家人,祝福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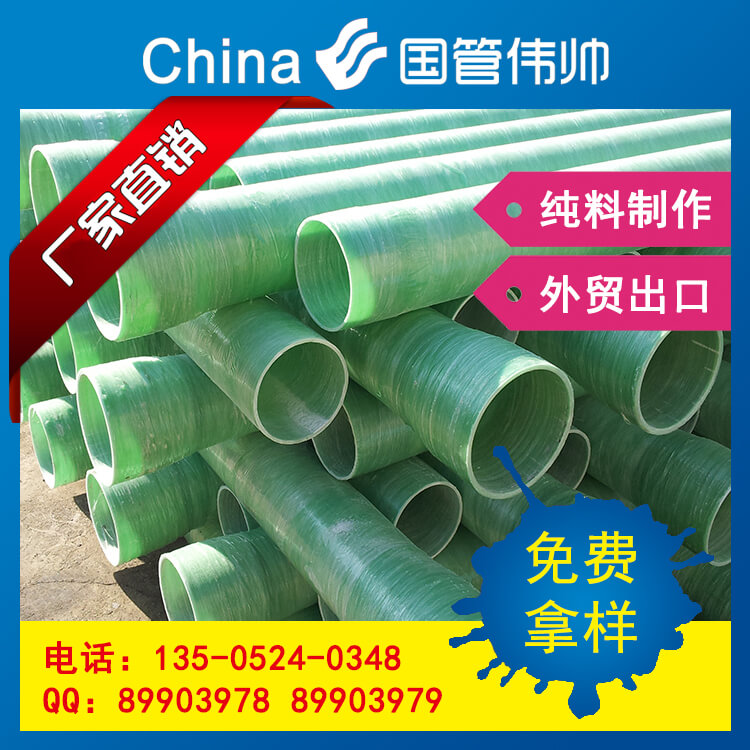
|





